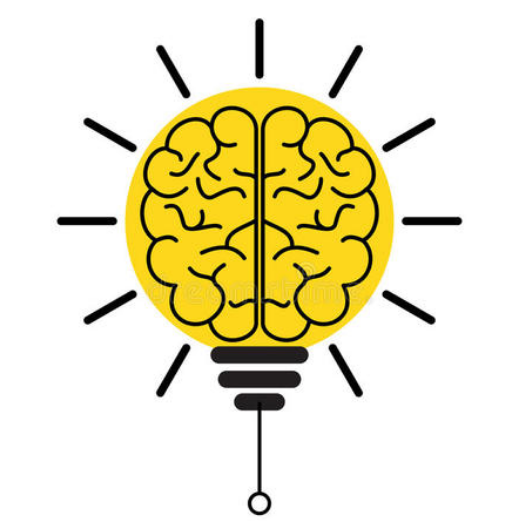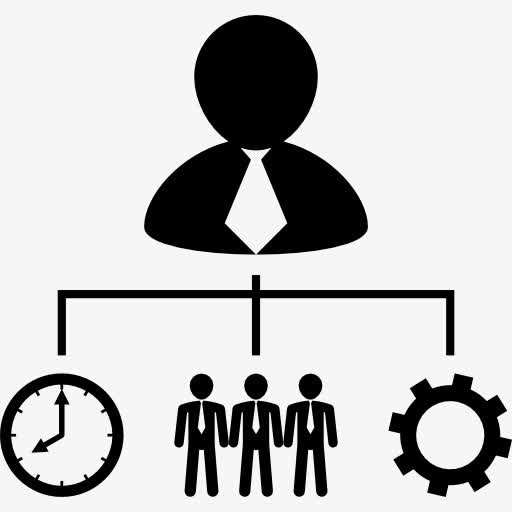“过番”史,一匹尘封的绸缎
近段时间,一直在做关于潮汕文化的资料,涉猎范围如漾开的水纹,一点点地扩大,一步步地深入。轻轻地敲开潮学之门,小心地举一举步,似乎是刚刚迈进去了,探询般地寻访着潮文化的前世今生。它像一袭华美的旗袍,扎染着花色斑斓,浸润着诗意的辉煌,也糅杂着历史的沧桑。像洇湿在水中的墨痕,流转暗合成一段特殊的历史,生生地衍出一款特殊的文化来——
“过番”的历史和文化,如一匹尘封多年的绸缎,透过薄薄的一层尘埃,那闪烁着的华光还是凉凉地逼仄着你的眼,你的心,颤栗着你的灵魂。潮汕地区地狭人多,又因着背山面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许多潮人迫于生计,毅然选择登上简陋的木制红头船,劈波斩浪,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远赴异地谋生。离别的码头,氤氲着惆怅,弥漫着愁绪,父母妻儿泪流满面,千叮咛,万嘱咐,“钱银知寄人知转,勿忘父母共妻房”。此去经年,山重水复,何日更回转?前路漫漫,生死未卜,长歌当哭,万般无奈轻别离,心慌慌,意茫茫。
浩浩汤汤的过番大军一波又一波,如浩荡澎湃的海潮,汹涌而去,带着粗砺,带着伤悲,带着对前路无从知晓的慌乱和迷茫,牙一咬,心一横,从此,他乡变故里。“卖咕哩”(卖苦力),做长工,披荆斩棘,翻滚摸爬,艰苦创业,为的是拒绝“等饿死”,为的是父母共妻儿,再苦再累再艰难,也得孤身一人去担当。潮汕歌谣有这样直白的写照:“来到暹罗,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番仔擎刀。”“人呾晕船吐胆汁,做人苦比胆汁多;夜来写信回唐山,笔仔擎起目汁落。”当地人的歧视、排挤和非人虐待,像针像刺又像戟,摧残着肉体,打压着精神,却依旧坚强地咬咬牙,用力挺一挺,撑下来了,是不屈;撑下来了,就有出头的一日。“日出乞日曝,雨来去雨沃。所擎大杉桁,所作日共夜。草底有毒蛇,山顶豺狼恶。”——血泪斑斑的过番奋斗史,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不外乎如此吧。
一封封闪烁着金光的侨批跨洋越海,飞回了唐山,飞回了故里,华丽丽地飞进侨眷家属千万家。虽说“番畔钱银唐山福”,可又有谁能体悟到这一封封记载着思念和牵挂,承载着改变贫穷改变命运的侨批背后的血泪和辛酸呢?
“过番”,辉煌时是一匹惊艳四座的绸缎,扎染着梅竹,清奇;编织着牡丹,雍容;刺绣着彩凤,典雅;交织着祥龙,华贵。斑斓绮丽,五彩缤纷,细滑柔软,冰丝清凉。在那艰难险阻的岁月里,飘逸,丝光,贵气,华丽,凌驾于青云端,袅袅婷婷,亮闪闪地透出她的柔媚和诱人来。仰望着的旁人,啧啧称羡。
侨眷家属衣食无忧,光鲜亮丽,生活富裕,幸福指数杠杠的,羡煞没有番客的旁人。可是谁能清楚地知道这样闪亮着幸福光环的家庭里不为人知的苦楚和悲凉呢?
成千上万有着“过番翁”的潮汕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着过番男人的托嘱,上奉公婆,下育儿女,盼着日出盼日落,苦苦等待着出外谋生的男人能够早日衣锦还乡,一起琴瑟和鸣,比翼双飞。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望穿秋水,都还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潮水悠悠,柔肠寸断,千回百转。“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乱如丝呀,心如麻。
留守的潮汕女人重情守礼,恪守妇道,独守空房,“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月明寂寂,“罗衾不耐五更寒”的悲苦生活,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宽慰?“独坐莫凭栏”,幽幽愁怨上心头,“别时容易见时难”,“日日思君不见君”,恨薄幸,轻别离,“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栏。难!难!难!”留守女人的悲哀和凄凉,像飘着冷雨的寒夜里,伸手触摸着的绸缎,滑滑的,湿湿的,有点腻,有点细软,透心凉。忽一触,心湖倏地有飞鸟掠过,吃一惊,心分明地动荡着、碰撞着,柔波碎了一地。
执笔至此,忽地想起小时候陪着奶奶到过番人家家里的情形。每每见到从番畔回来的番客,奶奶总会急急地向他们打探自己那个失联弟弟的消息,一旦打听到有人见到他了,奶奶的脸,顷刻拧成花;音讯全无时,奶奶的脸,花儿在凋零,叹了一口气,长长的,久久的,特心塞。奶奶是长姐,手足情深,血脉相连,怎能不思量?年年岁岁花相似,庭前的燕子,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过番的人匆匆来,又急急走,奶奶却终其一生也盼不回她过番弟弟的身影。听说他在那边另立了妻室,留下家乡年轻的妻子和遗腹子,孤苦一生,花香半零落。老舅母长什么样儿,打小没见过,听说很年轻就过世了。想必是相思成疾,郁郁而终吧。那阴郁,那愁恨,那幽怨,自是凄凉无极限!
千般恨,恨别在天涯。“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与谁同?唯有泪千行。“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山长水阔知何处?离人泪,泪千行。“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燕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湿衣巾,湿枕衾,湿湿上心头。“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问君此去几时回?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时至今日,当我们还在盛情礼赞潮汕留守妇人恪守“女德”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为她们鸣一声屈,喊一声冤呢?“女德无极,妇怨无终”啊!违背人的自然属性的道德约束和规范,终究是值得质疑和声讨的。
用光阴浸润过的“过番”史,是一匹尘封的绸缎,春日沉沉,淡淡的阳光斜照着,弹起轻轻的尘埃,薄薄的一层,渗出老旧的苍绿,苍老的绿,苍茫的绿,惨淡的薄凉。恰若,那消逝的红头船,远去的历史,飞逃的岁月,一把把摸上去,凉意盈袖,是老旧了的呀!





002.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