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榴 ‖ 物语,对事物与世界的诗意采撷
安石榴,《在丰顺等你》作者。
旷馥斋
2018-01-02 09:30
物语,对事物与世界的诗意采撷
安石榴
一年多前,因为写作《在丰顺等你》一书的缘故,地处粤东客潮交汇地带的丰顺县,成为了我比自己的家乡还要熟知的地方,并由此持续熟悉和亲近了起来。此后,每次再去丰顺,我都有一种回乡的感觉,丰顺的朋友们,尤其是同样热爱文学的朋友,就成了我内心暗暗认定的乡党,诗人陈其旭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写作的历程上,陈其旭比我展开得更早,自结识以来,他一直是我保持着尊重及亲切的兄长。我阅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包括之前出版的诗集《水底的稻》和诗性随笔集《诗话人生》,以及不断见诸报刊的一批零散的诗作,并有过多次深入而愉快的交流。这次,他又将两年来的诗歌作品结集为《幸福就在拐弯处》,嘱托我为之作序,让我得以先行探寻他诗歌设置的“拐弯处”,快人一步地感受到他的“幸福”。
物与人的交拟
如果说诗歌是语言的隐秘建筑,那么字词、句子就是经过挑选打磨的砖块,意象、结构等就是意念混合之后的钢筋和混凝土,诗人既是建筑师,又是居住者,遵循自我认定的空间及美学法则,搭建试图受到时间光亮普照的语言之屋,并热衷于坐在屋子里不断地敲打。或许可以这样去看,一部诗集就是一个诗人在某个阶段工程告竣的屋宇,凝聚着诗人在此期间的心血、追求,包括趣味及享受。在对《幸福就在拐弯处》进行反复阅读之后,我依稀认清了陈其旭赋予这座语言建筑的风格,大致感受到了材料的质地,并仿佛触摸到了内在刻画的符号。在此,我愿意借助“物语”这一指认性的词语来展开个人的浅显的谈论,就我看来,这部诗集中的诗歌,无一不是状物为语、由物及意的,诗人通过对所见所闻的日常事物以及若隐若现的物我世界的观察,采撷下能够发生诗意传递的物语,构筑散发着自己气息和声音、思维与思想的诗歌宫殿。
物语是根据事物的一些特性、人们的习惯等,将事物拟人化了,或者将人的表达物化了,从而达到情感表述的需要。物语可以视作事物与心灵碰撞产生的共鸣,也可视作具有特殊转换作用的一种技法。在日本,物语是一种流传久远的文学体裁,意即故事、传说或杂谈。由此可见,物语进入写作,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有效的手法。既然物语的核心是拟人化或物化,是物与人的精神共振,那么,物与人的交拟自然必不可少,应当认为是这一手法的要旨,是事物、情景、情感等的有机联系与交融。从《幸福就在拐弯处》中,可以抽出不少这样的写作样本。
“一个莽撞的少年/将春天打翻”、“山路很长,一个人走/任阳光从肩上滑落/鸟的天籁在背后追。”从诗集一开始的《打翻的春天》以及被用作书名的《幸福就在拐弯处》两首诗中,我就清晰地看到了物与人交拟,可以判断陈其旭对此的看重,除了词语、意象等交织组合的延伸效果,从中还可看到场景化和时空感,窥探得出他的情感方向,借助物与人交拟而构成的情绪、空间错落,表达生命、人生的缅怀与感悟。再如“红灯笼一盏接一盏/点亮,像中年的心事/热烈而不晃眼”(《不肯下船的青春》)、“又一年过去了/我信任的硬盘也突然失联/做一个细心的人,配合时光/收藏起工作、生活的酸甜苦辣”(《旧年贴》)、“春天还在低处/你看到的我,是凋疏的/就像泰山上的树/只有光秃秃的枝丫”(《泰山上的树》)……这些不断闪现的诗句,均是由物及人或者由人及物、再进一步及情及意的触动和提升,呈现出诗人多感易动的性情,外层内层转换拓开的能力以及思索所抵达的深度、广度。
物与人的交拟,又并非简单的拟人化或物化,也不仅仅是拟人化和物化的交互,无论任何时候,技法的运用都只能是写作的进入和展开,唯有作品达到精彩与完美,其魅力方能显现出来,否则不是黔驴技穷,就是画蛇添足。我始终认为,诗歌是一种节制而完整的艺术,语言和技巧都不可轻率滥用,节制中又见结构及巧妙,是优秀诗歌的一种品质。从《幸福就在拐弯处》的部分诗歌,我惊喜地遇上了这样的品质,以《可以携带的春天》为例:“你看到茶山上的绿/铺上云端/折叠起来/每一片,都是/可以携带的春天……”在此,简净的语言带出交拟的力量,充分发挥了意象的作用,同时又渲染出场景化、情景化的效果。
物与物的叠加
诗歌是最具个性化及意愿化的,在很多人的诗歌写作中,都极少看到他者,“我”往往成为一首诗的中心,成为磁场正中的磁铁。当然诗歌中的“我”在大多数时候都不单纯代表人称,而更多是起着引导、推进或其他作用的代称,这已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常态。但是,不能不说,将“我”从句子中直接或间接隐去,让“他者”以主体的面目充分在场,在诗歌写作中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很可能会致使写作者把握不住方向。或许这并不能算作是一个问题,因为诗歌写作在很多时候可以把一切打碎。在这里,我想说的只是,在我为陈其旭诗歌所梳理的“物语”中,我察觉到另一种重要的手法,就是几乎完全以他者视角展开的物与物的叠加。
在物与物的叠加中,具有强烈的拟人化,同时隐现出一个暗中在场的“我”。这是我从《幸福就在拐弯处》这部诗集中相对于物与人交拟的另一种发现,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或许陈其旭本人并没有如此有意识地作出安排,他不过是自然而然地运用了自己的感受和方法,而我基于自己的阅读认知并为了印证自己的指认,未免显得牵强附会了,很可能有所偏离。这并无不可,一个诗歌写作者不可能时时预设一条轨道,一个读者也未必能够轻易触摸到作者的意趣,写作过程充满意外和历险,阅读也有着多重理解与可能。还是让我按照个人的解读,列举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物与物叠加的例子吧,如“银杏飞进阳台/召开色彩大会/空椅子上的霞光/转身走出草坪”(《静美无声》),银杏、阳台、空椅子、霞光、草坪,这些物象意象的组合,形成了色彩和光影的叠加,构成了一个陆离、静谧而柔美的世界;再如“阳光穿过冰雪/大地满足于自己的静穆/飞鸟收起鸿爪/不想惊动冬眠的鱼//你爱上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暖和”(《你爱上的世界》),由阳光、冰雪、大地、飞鸟这些自然界事物的叠加,衬托出一个安静祥和的场景,并延伸到自然生态上面,表现出和谐、温暖、爱及憧憬。
诸如这样的物与物叠加,看上去似乎是静态的,但却是动态的,因为整个情形生动而真切,更因为其中加入了拟人化的表述,开启了情怀的通道,打开了哲理的空间。及物的目的是为了及意,让物与物在语句中反复出现,不断闪动,诗意也就一环扣一环,获得更多的指向,抵达更广阔的境地。我注意到,在物与物的叠加中,陈其旭充分运用了意象的力量,在巧妙的起承转合中既显出结构的美感,又突出诗意的递升,试读这一首《大地隐藏它的秘密》:“花儿香,绿叶长/蝴蝶翩翩飞/鸟嘴里衔着的母爱/填满整个天空//大地隐藏它的秘密//你喜欢的佳丽/像春风一样短暂/她要你读懂祥瑞/然后,对万物心生感激”,本诗由物到物,再及人及意,最后又回到对物的体察,诗意空间及哲思理性就在其中渐次打开。
看得出,陈其旭试图通过对“万物”的体察,通过物我之间的沉思,从物性到人性、到灵魂的角度,表达个人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生的感悟。在诗集第二辑《一禅一味》中,最能体现了他的这一心境,堪称情怀和心灵的写照,流露了他对简约、宁静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单就开头的一个组诗《不可名状的香》,即可窥见他从中获得的内心平静及由此而展开的从容,不妨读一读这样的句子:“如果想象沿溪而上/你将听到鸟声/任性地挥霍乡恋/看到茶的前身/在雨雾中翘首企盼/等待这个夏日的午后/与你邂逅谈禅/然后,相视一笑”。
行走和乡土之歌
在这部诗集里面,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专门着眼于地方见闻及掌故的,收录于第三辑《风中行走》中。这些诗作,截取所去过的各个地方中一些细微但却能引发感受的事物,如一架水车、一座浮桥、一场雨、一棵树等等,进行不拘一格、独具慧眼的诗意采撷。在采撷与书写之间,陈其旭似乎有意忽略了那些众所周知地带着明显地方烙印的事物,而只是闪现一双掠动而过的眼睛,拉开一个诗意行走的身影,但在读罢诗作之后,又总能令人对那个似乎只是轻描淡写的途经之地生出印象。我认为,这种反习惯的淡化手法,与前面指认的拟人化、物化一样,同样体现出技巧的特点及魅力,如同水墨的点染和写意之道。
在行走的他乡之外,同时也不乏着眼家乡的诗作,如同打开一幅地方风情画卷,诗人的情感和情怀跃然纸上。就此,诗人黄昌成曾作出如此赞许:“陈其旭推销自己的家乡时不遗余力,对自己所写的作品则抱着几分谦逊。”在诗集第四辑《在水一方》,充溢着满满的“家乡的味道”,陈其旭写家乡风土人情、乡野村落、人与事,或飘散在或远或近的记忆中,或具体到火龙习俗、老榕树和古镇等,取材独到,特色鲜明,用情真挚,感人至深,形象、清晰地勾勒出切入生命和热爱的一方水土,表现出一个诗人讴歌家乡的应有之义和对生养自己的乡土的感恩之情。
“走一条未知的路/你褪去青涩、犹疑/拐弯处,就有幸福等你”,这是《幸福就在拐弯处》一诗中的句子,流露出一种成熟、洞悉之后的从容,陈其旭将这首诗的题目同时作为诗集的命名,表明他对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已有了期许,有了信心。我相信,这也是他在生活、人生之途上一路行进间发出的心灵之语,只要拥有诗心、情怀与爱,拥有对生命的真挚,对世界的领悟,在转身和拐弯之处,必然会与幸福欣喜相遇。
2016年10月/广州五羊邨
本文作者:旷馥斋
*作者系著名诗人、散文家,中国70后诗歌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
陈其旭:守望古村落(组诗)
等待是一支射不出的箭
呆坐在古村落里
你像一个能一动不动的塑像
看见朝霞,沿着石板路
细心收集旧时的木屐声
一群背着书包的孩童
从身边一个个依稀走过
将回声兑换为知识、实业和荣耀
在目光不可触及的地方
洒下新的快乐,爱和哀愁
阳光悄悄爬上屋檐
你相信时间才是它下降的梯子
一只啄食的老母鸡
咯咯地叫,好像也读懂了
你手中洒下的寂寞
这时,墙头上的花开草绿
春天正踮着脚尖赶来
团圆的钟声却未冷却
你的等待是一支射不出的箭
思念是弦绷得再紧
可以定向瞄准的靶心
也如眼前的云翳
无法拴住新年的烟花爆竹
无所系的心
目光从墙头上的草
一直下降到断壁残垣
铺满石头的小巷
斑斑驳驳,时光的快车
跑过了康乾盛世
又跑进一个新的千年
如果目光再远些
你会透过石桅杆的霞光
看到骑马的先贤
将一个家族的根
扎进鞭子指向的山坡
沿着族谱的沃土追寻
开枝散叶的大树
高挂着民间的光荣和梦想
秋风吹起,你寻找的乡愁
像墙根上垒起的石块
曾撑起一代代人的安康
假如能给它们一双手脚
你想亲手牵一个回城
让无所系的心
夜夜惦记家园的重量
五丛榕
——写给中国古村落丰顺种玊上围
阳光惊动水面的鸭子
池塘的水牛,反刍着传说
五丛榕漏下读书声、练武声
散开三百多个春秋的绿荫
远看客家汉子,近听潮汕方言
一个举人的诞生
添上种榕一棵的村规
无声的铭记,比烟花爆竹响亮
久远,一个宗族的荣耀
五个举人合力撑起
倒映池塘的叶子,仿佛
族谱里的书签,夹着旧时光
古寨的姿娘,用闲情拨开暮色
仰慕而来的游客
读出,一方水土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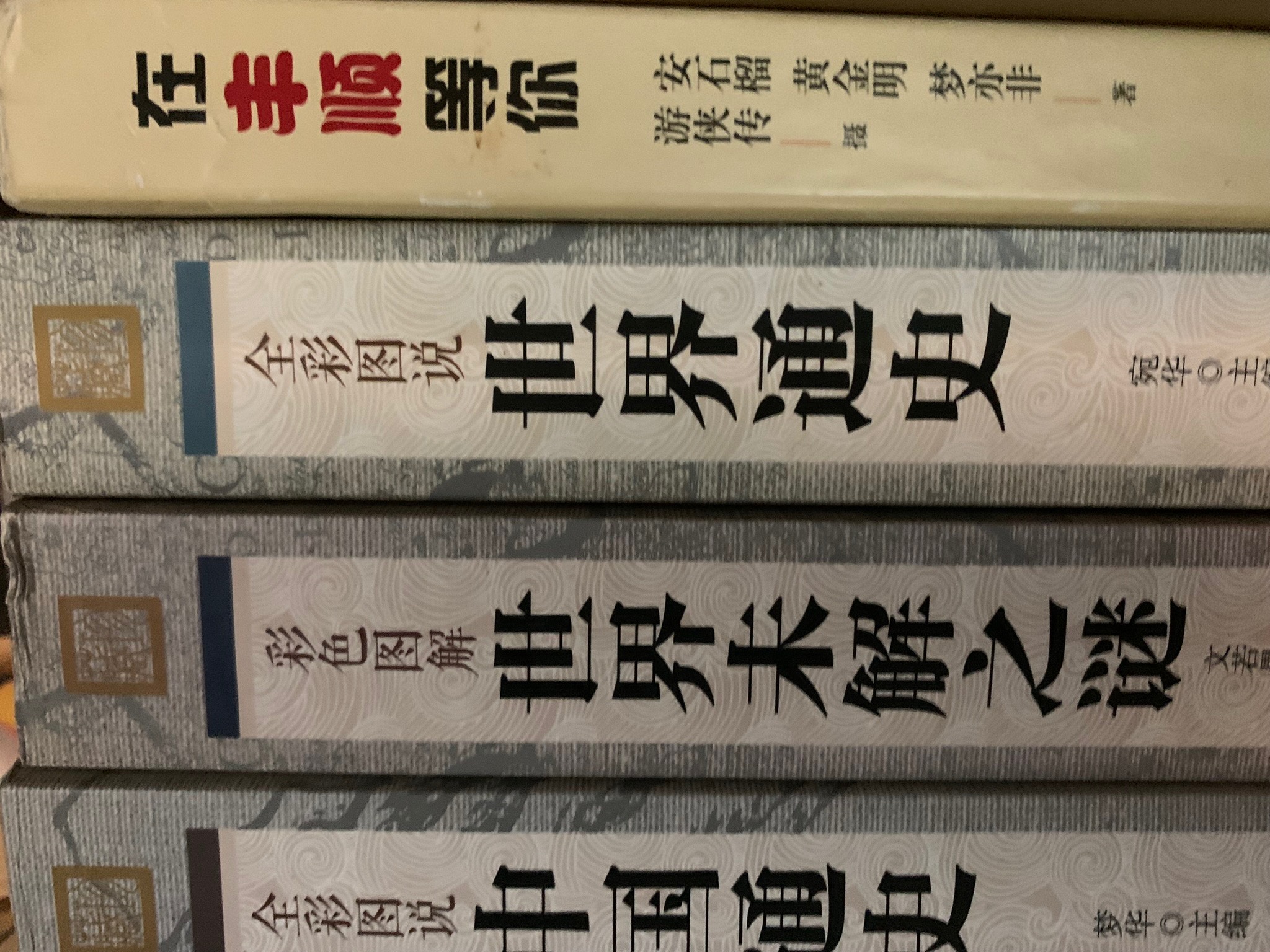



002.png)










